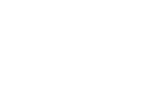導論及作品年表
【免費下載】《黑暗中潛行——張作驥回顧展》號外<呈現演員、場景背後自己的東西——專訪導演張作驥
陰翳禮讚——淺談張作驥與他的電影
文:安娜
說起台灣電影,總不期然會談到侯孝賢、楊德昌與「台灣新電影」;《悲情城市》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兩座巍峨高山,依然啓導著無數影迷與創作者。那幀侯、楊與吳念真、詹宏志、陳國富在西門町一字橫亙的照片,亦隨著「台灣新電影」的故事一同被神話化,變成了某種崇高意志的象徵。然而,在「台灣新電影」的戲都唱罷以後,台灣電影的故事該如何說下去呢?若數其後90年代最重要的登場影人,導演張作驥是不可或缺的名字。2011年張作驥獲頒國家文藝獎,小野為他撰寫了一篇素描文章,形容他「不是前浪,更不是後浪,他夾在兩波浪潮之間自生自滅,他是沒有結黨結幫的獨行俠」,可說一針見血。張作驥正是這樣一名性情中人,不在意拂逆潮流;他的電影,都依循自己的方法與信念去琢磨。其人其片,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張作驥1961年出生,父母都是國共內戰後撤退到台灣的廣東人。這個外省人第二代的身分,激發了他及作品對地域與語言的思考。他國中畢業後唸的是電子,直到20歲當兵前都未想過要把電影當做志業。在軍中他管戲院,放映的過程大家都不怎理會,有時候他更會亂放,把不同電影的拷貝接在一起,發現這樣子一樣可以看下去,赫然驚嘆電影的神妙。退伍前,張作驥搭錯車,要回台北卻去了台中,途上再三省思,終於毅然決定改考電影系。從文化大學戲劇系畢業後,他先後在《棋王》、《悲情城市》、《兩個油漆匠》等電影中任場記和副導演。他自言,期間受這三部電影的導演徐克、侯孝賢和虞戡平影響最深。1990年開始,他執導了幾部以青少年為題的電視劇,又拍了兩部有關少年犯的電視紀錄片《偷竊》和《結夥搶劫》,為他後來的寫實風格奠下基礎。
1993年張作驥有機會執導自己的劇本《暗夜槍聲》,但完成後卻被(來自香港的)監製粗暴刪剪,致令他拒絕在影片上掛名,並禁止它在台灣上映。1996年,他以800萬新台幣的低成本拍成講述居於關渡平原、學「八家將」的底層少年的《忠仔》。其後,他以「三年一部」的步伐,先後拍出在盲人家庭成長的少女《黑暗之光》(1999),及描寫兩名身處傳統大家庭與幫派生活夾縫的少年的《美麗時光》(2002)。這三部早期作品贏得廣泛讚譽,評論界對他的潛力亦抱著殷切期待。(盧非易點評《黑暗之光》時嘗言︰「張作驥是侯孝賢以後台灣最值得注目的導演。」)《忠仔》在亞太影展與釜山電影節都得過獎項;《黑暗之光》得了東京影展三項大獎,並入選康城影展的「導演雙周」單元;《美麗時光》則獲金馬最佳劇情片及入圍威尼斯影展主競賽項目。
就這個走勢看來,張作驥初期發展似是穩健和順利,成績亦足以傲人。然而,那段日子卻是台灣電影最慘淡蕭條的時期。影評人聞天祥回顧1990至2000年代的台灣電影發展,提到1995年台灣電影已呈衰落跡象:該年154部在台上映的華語片中,台片只佔18部(到2001年更只剩10部),而且水平亦遠遜往年。1997年台灣為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多次開放對外片進口拷貝的限制;在《鐵達尼號》的浪潮下,該年外片在台北的票房高達31億新台幣,較三年前增長100%。但反觀台灣電影在市場上的票房佔有率,從97年起至2002年長期連1%都沒有。張作驥才起步,所面對的其實就是這樣一個艱難和嚴峻的時勢。自《暗夜槍聲》不歡而散後,他明白到要有創作自主,就必須靠自己、不向大片商或財團靠攏、以低成本完成作品。拍《黑暗之光》時,他已經成立「張作驥電影工作室」,自購器材做同步錄音,從剪接到上映發行全部一手包辦。這種「百分百對自己的成品負責……全部都是自己意見」的獨立製片模式,不但成就了張作驥多部神采獨特的電影,亦讓他在台灣電影圈中佔有一個異常重要的位置。正當業界為資金來源與市場萎靡而苦惱時,他卻示範了以創作為本,仍可殺出一條活路的模式。他早在《忠仔》之後已志氣滿滿地說過:「我覺得拍電影的人應該是在創造遊戲規則,不是follow(跟從)遊戲規則,前人有的規則只是早點拍而已。所以我必須堅持自己的原創想法,否則不僅不倫不類,也沒有別人會幫你擔起責任。」
《美麗時光》之後,張作驥的創作路並不好走。接下來的《蝴蝶》(2007),本來有一大段關於日據歷史的篇幅是用動畫來呈現的,結果幾經波折都不能實現,電影推出後評論毀譽參半,票房亦不理想。在文化局的贊助下,2009年他拍成帶公益成分的《爸…你好嗎?》。作品由十個以父親為題的短片串連而成,勾勒出一幅來自不同背景、階級,但同樣愛惜家庭子女的父親肖像。張作驥作品至此暫別以往的灰暗齷齪,變得較為溫和,內容更聚焦家族故事,勻稱地兼顧不同家庭成員的心境。2010年的《當愛來的時候》寫少女未婚懷孕的心路跌宕,旁及親母與大媽,刻劃出三名兩代女性各自的困逼與辛酸。電影入圍14項金馬獎提名,是張作驥生涯的另一高點。2013年的《暑假作業》原本想拓展短片〈1949穿過黑暗的火花〉(2011),以動畫重現祖父輩參與金門保衛戰的壯烈場面,但因成本過高而未能成事。電影最後簡化成一個在城市裡被寵壞的小孩到山野與爺爺過暑假的故事。其後,他再度蛻變,2015年的《醉•生夢死》一方面回歸到早期常見的社會底層、黑道與暴力元素,另一方面又挑戰從未觸及的同性戀和情慾描寫。電影在敘事上的自由、情感之濃烈、演出與調度的亮麗揮灑,在張作驥的作品系譜裡達到另一境界。同年,他因被控性侵而判刑,監禁期間繼續創作,2017年夥同獄友,拍成千迴百轉、思念親情的短片《鹹水雞的滋味》。張作驥目前正在籌備新片《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講述家族眾人如何面對患上失智症的阿公。
張作驥並不以情節橋段取勝,看他的作品最感衝擊的,往往是戲中不同元素的反差對比。他的電影一邊有卑賤、渾沌和極端血腥殘酷的描寫(例如《忠仔》裡對忠仔亦父亦友的陳銘,因開罪對頭幫派,在忠仔面前給仇家亂刀斬死),另一邊則充滿細緻情感、陰柔,甚至魔幻的筆觸(再以《忠仔》為例,片末母親為家計到筳席上作詼諧演出,她自覺羞愧,不想兒子看見,把他趕走。不聽話的忠仔偷偷回來,瞧見母親在台上假扮俗艷的孕婦,看得無言出神,心酸的同時彷彿突然又多明白了母親的一點甚麼)。張作驥的電影世界及其力量,就是建立在這種不可思議的矛盾與張力之上。大概,愈是潛進黑暗,就愈能察覺亮光,他的作品有一種愈墮落愈美麗的傾向。我想背後的原因,大概是在邊緣生活、無勢無權的人,光是為了生存就要扭盡六壬,或逃亡、或拼命、或賣身、或啞忍,結果被激發出一種原始而熱熾的生命力。對於這種暴烈的現實境況,張作驥有時又會加入浪漫化的筆觸,使作品更意韻悠長。就如《黑暗之光》拍攝阿平在幫派打鬥中瀕死的鏡頭:鐮刀已經駭人地劈入阿平肩膀深處,他卻忍著一口氣走完最後幾步,鏡頭隨著他橫移,身後的天空突然滲出湛藍,地上燈光明媚,浪聲依舊。環境與調度的優美反襯著阿平的死亡,把他的絕望、哀愁,與太早終結的愛情,帶到一個超脫、凝煉的層次。
張作驥的監製高文宏形容過他︰「沒辦法做不誠實的影像。」求真,絕對是張作驥一以貫之的終極追求。很多人都稱頌他的演員很有生活感,往往能捕捉到動人的實在質感。由《忠仔》開始,他會邀請演員在開拍前幾個月與他一起生活,以日復日的親身體驗去代入角色;同時,他亦會藉此觀察演員,並按照他們的個性與變化調節劇本。這種準備方式相當耗時,但因為挑的都是非職業演員,他們沒有前設的表演程式或訓練(張作驥本身亦不喜歡那種很痕跡累累的演出方法),於是這種做法就成了提煉「真實」的不二法門。
這又直接引申出張作驥作品的另一特質:演員與他們的演出在電影中佔上一個十分突出的位置。細心觀看,不難發現影片的運鏡和調度,很多時其實都是為了配合、強調演員的表演而設的。而張作驥本身對演員細密的關心與注視,其實亦反映出他對他的描寫對象——那些在不為人知的暗處掙扎求生的人們——的關懷。相比起形式、技巧或抽象概念等命題,他更感興趣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物與他們之間的矛盾、掙扎與複雜的感情糾結。
張作驥曾不只一次以火車的比喻概括他的人生觀:「我們從出生就上了一班火車,這火車往懸崖開去,無論掉落懸崖的時間早晚,人終究要走;以懸崖作為人生的終點,這就是宿命。但是,火車遇站停止的時候,要下車逛逛還是留在火車上,便要看自己了。我想,重要的,還是去欣賞、參與途中的風景 。」張作驥沒有選擇,他錯過了「台灣新電影」的列車,卻在自己的時代裡一步一步走出了亮麗的軌跡,完成了多個無可取代的優秀作品。在他的電影世界裡,隨處都可以見到命運的暗影與潛伏於陰翳處的殘酷醜惡,而能否在最惡劣的事物裡看出可愛甚或是奇妙的東西,則取決於每個人的眼界與抉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