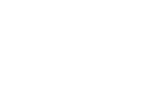前言
對大部分電影研究者(不論中外,包括影評人、學者、理論家或歷史學家)來說,香港的「功夫電影」的最大價值,似乎都是它們提供的感官娛樂效果(通過刺激燦爛的搏擊、悅目得有如舞蹈編排的拳腳招式,來作出突破人體體能限制的表演,並配以巧妙的道具設計和意想不到的笑料),即使偶然會涉及其他主題(如男性情誼、武學的道德層面),也罕有地會有論者願意進一步探討這批大多由武師或武術指導轉當導演的視野或世界觀,更遑論他們在電影語言上有任何的探索、拓展或貢獻了(最多只是指出這些作品如何提醒他們電影的原始樂趣(primal pleasure)的重要性)。
顯然的,劉家良的電影遠超於此。大衛博維爾(較諸其他學者都要)精警的地方,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劉家良「不是以功夫為手段、以拍片為目的,而是利用電影把功夫這個他所崇敬的傳統記錄與保存下來。」(見《無懈可擊的片場導演》一文)這個得追溯劉師傅的背景與出身。跟其他上述同時期的「武師導演」們(原諒我使用這個便利的說法)不一樣,劉師傅出生並成長於一個正統的武術體系(門派)與家庭(父親劉湛是南派洪拳傳奇人物黃飛鴻的第三代弟子)。武術對他來說,彷彿就是與生俱來、流在他血液裡的遺傳性因子,而他的使命,就是把它發揚光大。除此之外,武術又是一種生存的方式——他幾乎在每個場合,都會毫無保留地表達對父親的崇拜,因為後者憑著一身武功建立了他的事業(開設武館、在電影圈裡闖出名堂)與家庭。跟他父親不一樣的,是劉師傅最終放棄了開武館的念頭,而全身投入電影的世界(他與張徹鬧翻後,其實一度想去美國開武館,不過最後被「邵氏」挽留下來,當上了導演)。我覺得這個抉擇除了是因為電影在金錢和聲譽方面的回報較吸引外,更重要的是劉師傅發現了電影原來是示範和說明武術的本質與精神的最適貼形式和工具。這要從劉湛在兒子15歲時便帶著他進入片場拍片說起。那是1950年發行的《關東小俠》(顧文宗導演) 。這之後,由當臨時演員和替身到龍虎武師、到炙手可熱的武術指導、再到導演前的25年間,劉參與過的電影超過了230部 。這些電影包括了古裝武俠(以刀劍為主)、民初拳腳和時裝警匪等不同類型。劉師傅負責的是武打——即動作——部分,而動作(action),正正就是電影——movie、motion-picture——的本質。我更相信的,是在200多部電影之後,劉師傅進一步找到的,不僅是武術與電影之間的共通點,而是怎樣透過鏡頭/鏡框裡可收可放的空間、故事和人物,把武術的一放一收和它的學問與涵意(一種哲學),闡述與展現給更多人看。與他相反,其他同期的武師導演幾乎全都出身自北派的京劇學院。無疑的,跟正統的武術門派一樣,這些京劇院校(不論是私人性質,如于占元、粉菊花,抑或國家機構)的訓練都十分嚴格,也包括很多武術的元素。大多數學員並都是從小開始(9、10歲)就接受全日制的學習(很多都住在學校),但他們學藝的最大目的,卻不在於承傳(武術),而是表演(舞台與電影)。這解釋了他們的電影為什麼都往往淪為一場沒有核心的雜耍騷(雖不乏精彩),而劉家良卻不論在敘事的形式、結構抑類型的規範上,會不斷有所顛覆、突破與發展。在這一點上,在港產動作片的範疇裡唯一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就只有胡金銓——去年「鮮浪潮」焦點影人的對象——了。二人一南一北,復充分反映出香港電影的廣度與宏度。能夠連續兩年舉辦他們的回顧展,真可說是一件最美妙的事情。
劉師傅的電影,可說的還有很多(諸如對權威/極權的堅決反叛、對學養的不懈追求、對不同領域的知識的吸納與包容、對年輕人的愛護與信任),限於篇幅,這裡就不細表,留待大家在戲院裡細心發掘了。是次放映,必須感謝的是翁靜晶博士的支持,還有是劉師傅的一眾演員與弟子的參與。是為前言。
(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