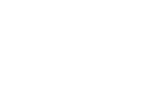序
《各位觀眾,我係楚原:楚原電影回顧展》這個構思,是在2019年我們完成《亂世俠客行——胡金銓電影回顧展》後開始醞釀的,當時已預見(對「鮮浪潮」這樣一個微小的民間組織而言)它的規模不會很小,我們能否負擔已是一個疑問;再加上楚原導演畢生的龐大作品數量,光是看片已是一項不大不小的「工程」,更遑論篩選放映片目的標準、種種資料蒐集的工作。此外,我們缺乏人手,每年大部分時間都要投入短片節的籌備和管理。在策展方面,尋找其他合作者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由50年代中旬開始,楚原一生跨越了香港電影最重要的粵語片、國語片和港產片時期(後者更是由他在1973年拍攝的《七十二家房客》揭櫫的),晚年在電視處境劇和劇集裡的演出更使他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對這幾方面都有一個通盤認識、願意擺脫/釐清一些過時或已經證明未必準確的觀點的研究者/評論人,而又可以騰出相當時間來的,坦白說並不多。然後,就是社會出現了變化和產生了疫情,「焦點影人」這項目也只好把焦點先集中在其他導演身上了,直到——不幸地,在2022年2月21日,楚原導演離世了。我們決意立刻付諸行動,即使在沒有很好的條件和準備下,開始進行策劃今天這個回顧展。過程中,我們獲悉香港電影資料館與香港電影導演會將合辦一個「玫瑰.蝴蝶.紅葉——再探楚原的秘密花園」的節目,選映他的13部作品以茲紀念。雖然將來的節目內容肯定會有所重疊,但再三思量後,我們還是繼續原來計劃。楚原和他的電影實在太需要我們多一點認識,特別是年輕觀眾。所以在平衡了各種考慮後,我們訂出了連同「參考電影」,共放映30部作品的範圍。
但事情的進展還是要比我們想像中困難,最主要的是牽涉大部分粵語片的版權及放映物料問題。粵語片版權分散得很厲害,部分版權持有人均已不在人間或離港多時,使我們用了很長時間和耐力,逐一追尋承繼人或轉讓者,以取得放映同意,滿足物料持有機構的要求;但如何取得可供目前高質數碼化影院接納作為放映的物料也不容易。儘管現在這些問題都獲得了解決,但仍希望觀眾對這些作品在影像和聲音上的缺陷都會予以體諒——這個也是我們最愧對所有粵語片先驅者的地方!〔如果每部粵語片都可以得到如「南洋三部曲」(均出品於1957)般的悉心修復和處理,那就太幸福了!〕最後要深表歉意的,還有我們確實沒有更多的時間和能力,在不同層面上提供更豐富的資料給大家參考。30部電影39場的放映仍是一大局限,如果可以容許的話,我們其實還希望節目可以包括《椰林月》(1957)、《九九九海灘命案》(1957)、《捉姦記》(1957)、《奸情》(1958)、《紫薇園的秋天》(1958)(楚原在以上作品全部是編劇)、《《湖畔草》(1959)、《昨夜夢魂中》(1963)、《大丈夫日記》(上集)(1964)、《黑玫瑰》(1965)、《蜜月》(1965)、《問君能有幾多愁》(1966)、《黑玫瑰與黑玫瑰》(1966)、《玉女神偷》(1967)、《嬌妻》(1967)、《冷暖青春》(1969)、《浪子》(1969)、《火鳥第一號》(1970)、《錄音機情殺案》(1970)、《玉樓春夢》(1970)、《龍沐香》(1970)⋯⋯這名單見證了一生拍攝超過120部作品的楚原,其中起碼有一半或以上都是佳作以至傑作。這樣的成就在香港確實無出其右。
有論者把楚原定性為一名典型的「片廠導演」(Studio director)。無疑的,在他經歷過的國、粵語片兩大時期中,他的電影沒有一部不是大部分在攝影棚中完成的〔實景佔比例較大的是他停止拍攝粵語片前兩年的《冬戀》(1968)、《浪子》和《冷暖青春》;加盟「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後,更只得一部《舞衣》(1974,約有60%的實景)〕。攝影棚擁有的先天性便利,使楚原可以在他的室內佈景——特別是主角的居所,不論富貴、中產以至貧苦——有一個寬敞的空間來裝飾和陳設,讓他發揮他對歐式宮廷或宗教建築風格的鍾情,以至他最愛掛在口邊的「意境」,所以才引申出「玫瑰.蝴蝶.紅葉」等標籤性的評論字眼。但這裡想指出的,是粵語片時期的楚原,其實一直保留着對社會現實的敏感和意識(這應該是承繼自他父輩一代對電影背負着反映現實和教育觀眾的責任的一套信念),只是到了他獨立當導演後,他所面對着的(或對他而言,他最關注的)「現實」,已不再是封建制度中的階級壓迫或經濟分配上的不平等,而更多是在個人理想的追求下、藝術與商業、個人與制度、開放與保守等種種思想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絕對是勇於表達自己的,即使有時用上十分直白的言辭(但影像和敘事結構上卻是多變的)。很可惜的是在當年比他更西化、更直接循多方面接受西方思潮衝擊的同代年輕人眼中,來自傳統粵語片、並仍在這個傳統框架下創作的楚原,不免顯得不足,甚至可能有點兒老套。這份不無偏頗和隔閡的印象,在今次重刊的《楚原訪問記》中隱約可見。我懷疑今日的年輕觀眾一樣未必可以消弭這種成見(甚至可能會變本加厲,覺得「好笑」)。我想提出的,只是楚原在這些電影中揭示的人物處境,在很多情形下,與你、我面對着的(時代)矛盾,其實真的沒有太大的分別。
所以正確點說,「片廠」真正對楚原造成一種封閉式的局限,是他進入「邵氏」之後,不單是在邵逸夫(和後來方逸華)的單一政策指令下,他只能不斷重複拍攝古龍(或相類的,如金庸、黃鷹)的古裝武俠片。有一點是被普遍忽略的,就是在粵語片時期裡,不論是在開始時的「光藝製片公司」或後來自組的「玫瑰影業公司」,楚原擁有的創作環境和心態都是高度自由的:大部分時間都可以自行決定拍甚麼題材、說甚麼故事——直到「邵氏」。在那裡,他應該是首次感到挫敗、感到被牢牢的箝制、感到妥協和隨波逐流的無可奈何、感到金錢和權力的「重要性」、目睹,甚至可能親自體驗過,比在粵語片時更大的腐敗。之所以他喜歡古龍,覺得和他的小說很合襯,是因為古龍最擅長寫的,正正是江湖中的險惡和權力爭鬥、武林中沒有人可以信任而導致的孤單感、和幾乎沒可能擁有的真摯友情和愛情。這次有一部考慮了很久是否應該選映的電影,那是他在「邵氏」拍攝的最後一部武俠片——《愛奴新傳》(1984)。那不是一部古龍小說,而是重拍被公認為他最好的「邵氏」作品——《愛奴》(1972)。不過他的創作動機並非為了要重複自己的成功,而是刻意地要把它摧毀,把它拍爛。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影片都不忍卒睹:拙劣的美術、惡俗可笑的色情場面、流水作業的打鬥、錯誤的選角。那不是導演或其他部門的能力出了問題,而是創作者向操控着他藝術生命的掌權人作出的消極反抗和報復[1],是一次過傾瀉而出、幾近殘酷的犬儒發洩。最後沒選,多少也是因為不忍。從這個角度看,他在「邵氏」片廠裡搭建出來的那個沒有年代、是非黑白含混不清的世界,一點也不乏它的現實意義。只是在當年(70年代中期以降,香港經濟日漸起飛,直至變成一個商業主義掛帥的都會)的氛圍中,似乎沒有幾個人留意到罷了!
這次放映節目結束、待大家對楚原有多一點認識後,約在8月底,我們會推出一個後續的「楚原電影再讀」的小課程,將設五個講座,邀請學者和評論人就不同範疇和切入點,輔以幾部今次回顧展中因聲畫質素問題未能在戲院裡放映的「漏網」作品,再深入討論楚原電影的意義。敬請留意「鮮浪潮」的官方發佈。
特別感謝楚原導演的太太南紅小姐、公子張詩樂先生和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大力協助,還有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使回顧展終於得以在拖延了一年多後與觀眾見面。感激。
策劃:舒琪
[1] 情形有點與他演出、譚家建明執導的《雪兒》(1984)相似,但少了那份偽善。見《雪兒》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