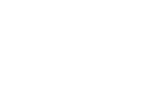批評的標準(文/梁濃剛)
批評似乎總是以分歧的居多,尤其涉及當代作品的時候,更難有所謂一致的評價。如果有留心美國的電影評論,不難發覺每年總有兩、三部電影會特別的掀起輿論的高潮,而在這個高潮當中,就可以看出所謂批評的標準,大多時候只是因人而異。而絕對好的作品其實絕無僅有;只是較多的人說好,或較少的人說不好而已。但是,這種分歧的現象並非是一個理想的批評氣氛。理想的批評應該是批評家共同培養出一個普遍的、合理的標準。只有在這個標準達到之後分歧的意見才可以說是百家爭鳴。否則,只能說是一團糟而已。
今年的例子是《流寇誌》(The Wild Bunch,1969)。本片在美國公映後所引起的激烈反應,情形和前年《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1967)相彷彿。兩部電影都牽涉到了暴力的問題,兩部電影都有慢鏡頭表現死亡的手法。而這兩個問題都無可避免涉及到了一種「限度」的標準,也是影評人爭持不下之點。
只要拿起任何兩篇《流寇誌》的評論,即可以看出影評人對這部電影意見的迥異程度。繼續寫其貶斥性影評的尊西蒙(John SIMON)認為本片既非最好[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雲信肯比(Vincent CANBY)所說],亦非最劣[如《紐約》(New York )雜誌的茱迪克麗絲(Judith CRIST)所言]。他認為《流寇誌》是一部重要的劣片(An Important Bad Film)。尊西蒙並非一個隨便作字面上遊戲的評論家,這點不用懷疑。如果你是一個《新領袖》(The New Leader)的長期讀者,當然會知道尊西蒙絕少對一部影片作正面讚賞的作風(所以他寧可讚森畢京柏是一個背後的推鏡大師 Master of the Rear Tracking Shot)。他覺得本片導演的立場較阿瑟潘(Arthur PENN)的可取(他指責《雌雄大盜》過分同情Bonnie與Clyde的行為),但是《流寇誌》的慢鏡頭及閃接式的蒙太奇手法,雖然減少觀眾對屠殺現場的殘暴感覺,但影片畢竟流血太多了。There’s too much gore in the film!他認為畢京柏的慢鏡頭死亡,實在等於市川崑《東京世運會》(1965)中撐竿的跳高選手越過橫木後,倒向沙堆中的慢動作一樣。慢影像並不強調勝負的意義,重要的是表現選手的那種體育精神。但是,在一個死亡的場合卻何「體育精神」之有?他認為此類的殘暴行為並沒有甚麼光榮的地方。
雖然尊西蒙的反對理由能夠自圓其說,而且從中可以看出其品味的態度及取捨的標準,但其他的評論卻多是以主觀的判斷為代替,只說流血太多了,而未有從表現的手段入手。從影評人對《雌雄大盜》、《流寇誌》的意見不一引出了一個批評上的問題:究竟作品表現(暴力)的限度有沒有標準可言呢?
而批評的困難便在這裡。假若真有這一標準的話,我們只要把《流寇誌》拿來比度一下,是否過於殘暴的爭執便可迎刃而解。但是,批評的本身並非是一項量度的過程;批評乃是以判斷為目的;是先有了判斷,然後才可以從這些判斷中顯現出一個標準來。但,這樣我們又返回一個批評家的個人立場上。假若你是一個實證主義者,你當然強調每個觀眾本身感受的重要性。但,既然你不能把《流寇誌》所有觀眾的感受統計出來,批評豈非不能建立起一個標準,而只能變成各持一說,或者索性要每個觀眾自己決定?所以,最後的問題還是批評風氣的問題。理想的批評現象是每個批評者都不應孤立及各自為政.批評界如果能夠多作互相參證比較,衡量作品的標準自然會趨向於一個普遍的、合理的方向。
美國影評界意見分歧及各自為政的現象,近年已有很大的改善。(其實批評甚少是一致的,但這裡的「分歧」是指其標準的凌亂而言。)《紐約時報》的克魯華(Bosley CROWTHER)退休之後,也很少再有獨斷的言論出現。前年更有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的組成,互相討論及容納對方意見的風氣確實日漸廣泛。餘下來的問題便是每個批評家都有其自身的批評方法及不同的背景修養,當彼此各據立場的時候,會不會造成一種品味標準的衝突呢?
這只是一個很粗略的說法。所謂Standard of Taste往往在對立的情形下會有更具體的顯現。譬如當我們從《流寇誌》的爭論中回過頭來,許多粗製濫造的意式牛仔片已經引不起我們的興趣。作為一個影評人,你可以選擇的立場實在很多。你可以建立一套理論或者有系統的思路,把電影當作整體的研究對象,這樣你批評每部作品的時候,主要的工作便是把它歸類或者列分,例如沙里斯(Andrew SARRIS)的方法。或者你可以是一個某些人所謂的Violent Critic,對每部作品提出最終的、特別的判斷,隨時套用新的觀念,例如尊西蒙的做法。當然,任何的批評方法都有它的限度,沒有一個評論家可以做到盡善盡美。譬如沙里斯的毛病是有時會陷於故步自封,未能迅速的接受新的導演。他分析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鶴士(Howard HAWKS)的作品可以令人折服,但他卻指米克尼高斯(Mike NICHOLS)的電影技法起碼抄襲一打以上的導演,但當一個人能夠抄襲十二個導演的時候,這已經不是抄襲這麼簡單了。又譬如尊西蒙有時會缺少透視的判斷。(他曾盛讚保哲農(Serge BOURGUIGNON)的《星期日與西貝兒》(Sundays and Cybele,1962),但該片在(法國)新(浪)潮作品中顯然不算出色。)但我們需要沙里斯的方法來提供一種電影整體的面貌,也需要像尊西蒙的一類批評來引發新的看法與思想。不同立場的評論依然可以建立出一個普遍的標準,問題是評論者能否表明其取捨的標準及品味之態度而已。
(原載於《中國學生周報》第901期,專欄「訪問鏡頭」,1969年10月24日,頁11。文章經統校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