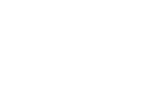序
文/舒琪
「鮮浪潮」在4年前開始增加的項目「焦點影人」,第一個考慮聚焦的對象,其實就是森畢京柏,只是後來資源有限,僅容許選映少量電影,畢京柏畢生拍攝的長篇電影雖然不算多(14部),但若只展出小部分,終究是個遺憾,遂改以托迪希恩斯(Todd HAYNES)的作品做主題。累積了4屆經驗後,我們決定重拾初心,回到Peckinpah-land(畢氏疆土):除了14部作品全數展出外,還添加了兩部一港一西的「參考電影」:杜琪峯的《放‧逐》(2006)和阿瑟潘(Arthur PENN)的《小人物》(Little Big Man,1970)。前者,是因為片中的人物關係、處境、以至氛圍、情懷都顯著地受畢京柏的影響;後者則是緊接着《流寇誌》(The Wild Bunch,1969)後推出的西部片,有很多地方可以互相比較,有助我們對這個美國荷里活專有的類型片在它日落黃沙的最後歲月中有更多的理解。
依然是那個問題:畢京柏的電影對當今香港年青一代的電影觀眾與作者有甚麼重要性嗎(尤其是上面都說了,他專長、並矢志不渝的西部片,早在70年代便趨沒落)?其實不盡然:我們一直堅信,時間是對作品最嚴格的考驗。雖說作品其中的一個重要性,是它對當下社會和時代的回應,但時代的步伐卻永遠是向前走的,一旦改朝換代,肯定會使作品產生出這樣那樣的距離,只有某些具有永恆的價值觀或先鋒意義(包括形式上的突破或實驗)的作品,方可經得起時間的測試,一樣能夠引起觀眾的鮮活感受,在隔代的時空裡找到相關的啟示。今天看森畢京柏的電影,即使是最陌生的西部類型,相信也一定能夠感受到一種絕不陌生的精神,那就是一份不管時代怎樣改變或被取代[在電影中往往是科技和新資本主義如何取替馬匹,如《荒漠怪俠赤手闖天涯》(The Ballad of Cable Hogue,1970),明文的法律如何代替槍桿子平息紛爭,如《流寇誌》],都改變不了個人對原則[如《亡命大煞星》(The Getaway,1972)、《摩登牛郎》(Junior Bonner,1972)]、信念[如《大丈夫與小人物》(Pat Garrett and Billy the Kid,1973)]與尊嚴[如《《大丈夫》(Straw Dogs,1971)]的堅持,還有是對信諾的承擔、愛人的守護與家園的保衛,誓死不屈。所謂Last Man Standing,意思就是要挺拔着身軀,戰到最後一刻。真實裡,畢京柏跟只談市場的大片廠的抗爭,即使幾乎從未佔過上風,但仍持續了一生[直到最後一部作品《週末大行動》(The Osterman Weekend,1983),還是在重剪時被fire掉]。另一場鬥爭,則是他與自己的身體:長期的酗酒與藥物,雖然經常使他情緒失控,但卻是他抓緊創作力衰退、和時間競爭的唯一方法。很tragic,但也很heroic。這樣的一份貫徹始終,希望在大家往後的電影路上都能用得上。
不無傷感的說,畢京柏死後的這麼多年,雖未至於被遺忘,但被認真審視,重新公正評價的情況並不多。是次全展更可能是整個亞洲的第一回。畢竟快接近40年了,在較年輕的評論群中能找到對他有深入研究的並不多。幸好當年他撼動世界影壇時,眾香港影評人中不乏長期關注着他的,其中寫得最有見地和最精彩的,莫過於吳昊及梁濃剛(後者剛在本冊子截稿前不幸離世)。二人風格各異,前者洗練嚴峻,後者灑脫儒雅,共通點是均廣閱西方論點、經小心比對過濾才下獨立結論。可以想像的是,文章在當年嚴重缺乏工具軟件、對電影畫面的掌握全憑觀影的次數與集中力等情形下,始能完成,由是特別珍貴。這次有點不合比例地精選了多篇佳作,雖然跡近放任,但今天讀來,每篇仍擲地有聲,實在十分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