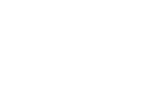論森畢京柏的電影(文/Sheila MEEHAN,中譯/阿芒)
森畢京柏兩部近期力作,《流寇誌》(The Wild Bunch,1969)和《大丈夫》(Straw Dogs,1971),曾引起惹人注目的極端性的批評。論者向畢京柏的才華提出質疑,每每稱之為「法西斯主義者」及「瘋子」,這是高度攻擊性而又曖昧得難以作辯的。但此等過於情緒化的批評正好道出了畢京柏作品的特色,多於指出其作品的質素。他的電影是感性凌駕知性,個性高於結構,意態先而形式後。
在新導演群中,也許是以森畢京柏和史丹利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這兩人,有最明顯的視野上的分異。如果電影就是影像的事情,它需要從無數個來源處吸收影像。寇比力克的電影是艱澀冰冷的心智的影像,他的電影好比是一個謎,向你的智慧挑戰,雖則我們會(亦應該要)對它的深度問題作出質疑。看畢京柏的電影,你會驚異於一切訴諸「感覺性」的影像,而觀眾牽涉其中竟達難以置信的程度。高潮是全然情緒上的。雖然他的作品在技巧上非常出色,但缺乏了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S)那種達成了技術上的建設之後的快感。畢京柏的優點是能夠以出色的剪接和攝影捕捉感覺。
森畢京柏的七部作品都拍得相當好。他表示不喜歡早期的《鐵漢與寡婦》(The Deadly Companions,1961)和《精忠英烈傳》(Major Dundee,1965),因為製片家和公司的干預,破壞了他原來的創作意圖。《午後槍聲》(Ride the High Country,1962)拍得溫婉、成熟,是《流寇誌》的前驅。《流寇誌》和《大丈夫》經常被論為是畢京柏兩部「血淋淋」的電影。無可否認,這兩部片(在技巧上)確是狂暴而駭人的,但影評人議論極端分岐,有說這種暴力是正當的,有說這是對觀眾情緒的剝削。
在分岐的議論中,又介入了畢京柏的兩部「文戲」,《荒漠怪俠赤手闖天涯》(The Ballad of Cable Hogue,1970)和《摩登牛郎》(Junior Bonner,1972),使得各據一方的批評家們大感迷惑。兩部片都是溫和而人性的,但缺乏了畢京柏的暴力片所引起的情緒上的一致。畢京柏仍有意拍攝些開懷的喜劇(如《荒》片的快動作鏡頭及《摩》片大鬧酒吧的場面),而亦有其價值之所在:它們有着好些美妙的演出,也包括了不少美妙但又參差的片段。
影評曾指出畢京柏作品的風格並沒有甚麼獨特之處,甚至沒有美感和吸引力可言(特別是他的暴力電影)。那麼,《流寇誌》新在哪裡?與眾不同的又在哪裡?當然,情節本身確是缺乏了獨創性,片終高潮爆發亦是電影結構的一往傳統。但影片並沒有硬着頭皮鑽新意,情節也與無數的美國西部片產生回應,但畢京柏給予極新的闡釋。早期的西部片,情節發展少不了正邪對立,而正的一方永遠站在勝利的一邊,雖則較近期已有轉變——正人君子孤獨而甚至絕望的奮鬥[例如《龍城殲霸戰》(High Noon,1952)的加利谷巴(Gary COOPER)],始能伸張正義,邪不勝正是大條道理,無人會對之質疑。《流寇誌》給你看到的卻是正邪難分而引人爭論。早期西部片所表現的朝氣和信心,在片中已煙消雲散,換來的全是日暮窮途的老人,他們無法適應一個轉變中的時代,被逼鋌而走險。
實在的轉變是影片呈現的意態和情緒。《流寇誌》的張力並不是產生於道德極端(正邪)的尖銳衝突,而是在恐懼、混亂和迷失的生命中。畢京柏最驚人的導演功力也許便是他能美妙地控制了這股張力。影片開首的一場戲(孩子火燒蠍子,流寇偽裝騎警入城,「法律」的一方卻是群被僱用的流氓)已經佈出了事態可怕的混亂局面,開場不久立即高潮爆發更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開場就是暴力,緊扣觀眾心弦――血淋淋的和事出意外的,卻成功地營造了一種突出的意態――在混亂的局面中顯出人類的無法無天。畢京柏幾番把這種緊張力提升近爆發點,但隨即鬆弛下來――都是片中人物的笑聲使然(個人和社會的挫折都在這種笑聲中渲洩)。甚至流寇之間亦經常產生緊張的磨擦,留意Gorch兄弟和Angel之間的衝突,又兩兄弟和那老頭各不相讓。這裡有個特別感人的場面:Pike舊創復發墮下馬來,他的領導地位受到打擊,看他堅定的,帶着一份沉默的尊嚴上馬,這一刻是畢京柏最優秀的表現。這場戲沒有半句對白,但情緒的緊張和複雜都在無言中美妙地流露出來。當Angel殺死了「他的女人」,那個投靠墨西哥軍閥的愛人,看來就要爆發出第二次血腥屠殺,但影片沒有這樣做。甚至後來流寇戲劇性的想援救Angel,氣氛是慢慢構成的,那股張力逐漸的收緊,直至血淋淋的混亂情景一發不可收拾。
以我所知,未曾有過一段影評文字提及從Angel之死到大屠殺的整個無言時刻。這一刻是使人驚駭無措的;畢京柏似乎是說:這些人是預定和必然地會在混亂中死亡,而且影像十分可怕。暴力是蘊藏於自然、時代和生命之中。這些人活在暴力中,但他們也是暴力,而暴力又毁滅了他們。
在畢京柏的幾部作品之中,我覺得《流寇誌》和它的視野(美國從個人的社會轉形型為工業社會期間所產生的混亂)是最尖銳的。這是一部複雜的電影——其影像和意義甚至可以維持多年仍能扣人心弦。
《大丈夫》是一部存疑的作品。技巧上它一定比《流寇誌》為高,畢京柏使盡剪接功夫的看家本領,仍未能展示出那股構成流寇的痛苦命運的「陰暗」的人性。畢京柏擅於利用演員的個性和美國電影的傳統。老牌演員如蘭杜夫史葛(Randolph SCOTT)和祖麥基利(Joel MCCREA)(《午後槍聲》),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和羅拔賴恩(Robert RYAN)(《流寇誌》),謝遜羅伯斯(Jason ROBARDS)(《荒漠怪俠赤手闖天涯》)及埃達綠翩奴(Ida LUPINO)和羅拔彼士頓(Robert PRESTON),還有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摩登牛郎》),都有很優美的表現。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在《大丈夫》演技精湛,但顯然是欠缺了個性——不像傳統明星如威廉荷頓等那樣保持着一份個人風格。美國觀眾看荷夫曼是看他的明星形象,畢京柏亦想到利用這點——他那種孩子氣,那種天真的異質和犬儒的作風。而荷夫曼最高的才華,是與角色打成一片,達至「忘我」之境,這對《大丈夫》一片卻是有害的。畢京柏不重劇本,而且向以簡潔見稱,但到了《大丈夫》卻無法給予中心人物一份深度。
畢京柏操縱電影這個媒介,顯出他的才華甚高。他長於透過細微的事物捕捉人類的情緒——一眸一動,和默默無語的一刻。畢京柏那些「浴血的芭蕾舞」式的場面贏來激賞,也惹來抨擊,但他很懂得把握細緻而人性的東西,這份才華卻受到了一般的忽視。
(Sheila MEEHAN,駐夏威夷影評人,本文原載於《影響》(台灣出版)第5期,1973年1月,頁9-11。文章經統校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