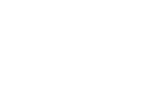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虛詞】專訪「鮮浪潮」導演曾慶宏:木已成舟,浪子回頭
文︰黃潤宇
報章︰虛詞
日期︰2019-4-30
訪問到了尾聲,紙頁上只剩下一條問題,幾經猶豫,還是用原子筆刪去了。眼前這位「慈眉善目」、講每句話都夾著兩聲笑的曾慶宏,實在讓人難以開口問他:「人人都話你好chok,你覺得甚麼才是chok?」
還記得2013年甫認識那位曾慶宏,人稱Eric Tsang,是位沉默寡言、導演架勢十足的cool guy;如今我們許久未見,一開口,談的卻是搬家與房租,真是始料未及。更「驚悚」的是,訪問期間Eric說了不下三次「我現在年紀唔細啦……」1988年出生的他其實剛滿三十,這樣的年紀究竟有多大,我不敢斷言;不過如今平添多重身份——作為導演,也作為兒子、丈夫——Eric展露的氣場確實有了很大轉變。
浪子回頭,修補家的裂痕
一年前,Eric Tsang以《下雨天》斬獲第十二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鮮浪潮大獎」;今年,他的最新作品《木已成舟》也被選為第十三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的開幕電影,可謂收穫頗豐。但與以往的社運主題不同,《木已成舟》是以家庭關係為主軸,講述一對因生活困頓而久未相見的母子故事,而這一切都源於Eric近來時常產生的、一種「大局已定」的感受:「幾年前還有保衛菜園村、有反高鐵,很多事情都在發生,之後更有雨傘運動,但再然後就很多聲音就消退了,『大局已定』的感覺愈來愈重。」縱覽香港幾年間的變化,Eric感觸頗深。
《木已成舟》本名就叫《大局已定》,但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未盡妥當,因為Eric並非想道出悲情定局,而是要思考大局已定之後,我們可以做些甚麽:「後來我選擇了最小的範疇,從母子之間的關係出發——母親和兒子都希望對方過得好,兩人的距離也並不遙遠,但偏偏各種因素影響之下,他們的關係只能這樣(分隔兩地久不見面)。這裡面有一種對於家庭的、不僅僅是愧疚的複雜感情。」歷經多次社會運動的Eric,曾經深刻感受過同溫層帶來的良好自我感覺和美好希望,如今運動聲息漸弱,躁動的青年人也該長大、該面對不同的聲音,回歸原生家庭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如今我希望撼動的,並不是與自己理念相近的人,而是原生家庭中與自己最親近的人。他們不需你重新認識,只要認真審視,就能令家庭有所變化。我希望能提供一個選擇。」
稍細心的觀眾,很快就發現片中那位生意失敗、獨居劏房的兒子熟口熟面,原來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周保松教授。Eric讓從未演過戲的周保松教授擔任主角,全因看到教授「年約四十、既不麻甩、又不高級」的特質,而這也帶有Eric自身經驗的投射。原本與父母關係極差,青春期就跑出來自己一個住,Eric困苦過也孤獨過,直到近年才下定決心修補裂痕:「到了二十八九歲,某個階段的事情已經經歷夠了,我不希望自己一直維持以前的狀態。現在看自己看夠了,知道最好和最壞不過如此,又不希望好的壞的都只有自己獨自面對——那不是我所追求的。」
那麼修補的成效如何呢?「來之前,我剛陪完媽媽看中醫。」Eric腼腆地笑著,現在他是因循自己作品理念的實踐者。
體會南音,無奈盡頭是祝福
而戲中那位客家母親,果然是以Eric媽媽為原型;畫面裡不少客家及粵地文化元素,例如客家住屋、藤籃、茶粿等等,也都是Eric自幼就熟悉的事物。而其中令人最記憶深刻的,要數兩段地水南音的運用——杜煥那句「但願係世間一切男女人事,人人一生快樂係過時天」遠遠飄來,黏著在母親孤獨的背影上,怎叫人不動容?
原來還在少不更事的時候,Eric已經聽過南音,一下就被那種與自己情懷相近的音樂所打動:「南音有一種憂愁,但憂愁到尾,竟然是祝福,儘管那可能是一記苦笑。一切從悲哀始,不過悲哀的是命運,不是世間邪惡;杜煥也不是控訴,只是慢慢述說。後來我慢慢發現多數南音收尾都有一份祝福,像是說『人生就是如此,聽完之後大家都要各自生活,希望你之後都過得好一點。』」片中母親與兒子都聽南音,南音也暗示著兩人的關係——都很慘,卻都希望彼此過得好,這種關係很複雜也很現實。為了能在電影中運用南音元素,Eric也費了一番功夫,最後幸得中大校友吳瑞卿博士引薦,向專精粵劇與南音的榮鴻曾教授取得了南音片段的使用授權,成就了這部電影的點睛之筆。
《木已成舟》的英文名是《A Thousand Sails》,千帆已過,也是監製別具匠心的設計。對獨居島上的母親而言,船隻來來往往,但沒有一艘上面有自己的孩子,悲傷是肯定的。但悲傷之外呢?沉默無奈之中尚有祝福,這是Eric想透過作品帶出的溫度。
創作之難,在鮮浪潮裡成長
從前討厭家庭、討厭短片,隨著年齡與心智的增長,Eric的態度也逐漸起著變化。然而也有些原則是他從不願意改變的,其中包括自己堅持的一套電影語言。
在拍攝和後製過程中,Eric抗拒過多剪接,更偏愛以長鏡頭敍事,《下雨天》更是運用一鏡到底的方法完成,這樣「前衛」的做法引起褒貶不一的評價,也令Eric面臨心理關口:「拍《無間道》那樣的商業大片是有格式、有準則的,但做我這樣的電影,是無法估計預測的。你或會說:『自己覺得好就可以了』,但談何容易呢?當面對不同的意見時,到底要如何說服自己?這也是我近幾年創作上的難處。」
說服之路,是實際工作砌成的。2013年,Eric憑《楊明的夏天》第一次進入鮮浪潮計劃,獲得的卻是永生難忘的挫敗經驗:「我是從那時候才開始了解到,拍戲要分不同部門、每個程序都要跟、整件事必須很完整。那是一次非常不好的經驗,正因如此,也成為了一次很好的經驗。」回想起稚嫩的自己,Eric也不禁莞爾。此後他開始化身為片場各種角色,連續七年以不同身份在鮮浪潮出現,做過監製也做過攝影師,直到去年才覺得萬事俱備,鼓足勇氣遞上新作:「以導演身份參與鮮浪潮計劃,每個人只有兩次機會,因此這是我最後一次參與了,我將之形容為『畢業』。」
功夫不負有心人,Eric不僅收到鮮浪潮的亮眼成績單,更收到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資助,終於要邁入電影創作的新階段。「在此之前,家人都知道我是做導演的,但我卻沒有參與過任何電影拍攝,連對自己都很難交代。當時常常都在想:我究竟在做什麼?」創作路上的困惑與不順遂,Eric仍然歷歷在目。
而如今,前路在嘗試與挖掘中逐漸明朗,他轉而開始關注起自己的責任來:「1988年生,我們已經不是最年輕的一代,但又有很多事情還未經歷過,但無論如何,我們經歷了香港非常重要的時代。」在Eric看來,不少同代人都在近年開始「默默做」,不再短視,而是在不脫離年輕聲音的同時,繼續找更長遠、更有意思的事。
「三十歲,好多人結婚生仔,點解呢?因為到了這個年紀,世界不再只有自己。」他笑笑口說道,下一站,要趕著與拍檔開始新工作了。如今三十歲的香港人,在青春時剛好經歷了最躁動的幾年;如今千帆已過,留下甚麽?唯有成長,用碎木搭成小舟,從此承擔起更多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