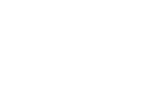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HK01周報】潮騷︰記第十二屆鮮浪潮本地短片
報章:HK01(周報)
日期:2018-4-30
作為一個同代的年青人,我想我對每年每一位參加鮮浪潮的新導演與及他們的短片,都深懷期盼和寄望。在一個年青人受到形形色色的誤解、質疑、壓逼的時代,我又何嘗不想見到我的同代人用影像堂堂正正的為我們爭一口氣,抒寫出這一世代紮在心頭無法言語的感受呢?我特別喜歡看到稟性不一的好作品/創作者走在一起,那種各有千秋的映襯較勁, 熱鬧又繽紛;他們向四方八面舒展自己的個性,說不定某一天就會從中走出一個頭角崢嶸的人物 。
比方說上屆鮮浪潮的《瀏陽河》(李駿碩導演,獲鮮浪潮大獎及公開組最佳導演)與《螻蟻》(任俠導演,獲公開組最佳導演及最佳攝影),前者文雅婉約,後者法度嚴謹而不減狂氣(一齣唱《鳳閣恩仇未了情》,一齣配上草東沒有派對的搖滾,兩者情調之分野可想而知),各走不同的創作與形式路向。又譬如2015年鮮浪潮的《後來怎麼了》(羅倩欣導演,獲公開組最佳電影)以緊湊的群戲與手搖鏡寫出刻下青年苦處,但另一邊廂卻有《長途列車》(吳雋導演)亮麗自信地以一場一鏡嘆喟舊人舊區的消散,兩片並列,可說是一幅豐富矚目的圖景。
今年鮮浪潮短片比賽來到第十二屆,取消了學生組,參賽影片減少了三份之一。從整體影片的水平而言,我覺得是稍為提升了(特別是在製作與拍攝方面)。說到今屆最優秀的兩三部作品,我心中也認為比去屆的得獎作品略勝一籌。較早前第十二屆鮮浪潮國際短片展已頒發了鮮浪潮大獎、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攝影等獎項予多部參賽本地短片。在個別討論今屆幾部短片佳作之前,我想約略提出綜觀十九部參賽作品後的初步觀察。
在每年二三十部鮮浪潮的參賽短片中,總有三至五部是直接或間接地指涉香港的現實政治環境。從數量上說,這些(籠統意義上的)政治電影佔總參賽作品數目的比例不高,然而,這一小撮作品,卻是多年來最受關注與討論的本地短片。這一類鮮浪潮短片的濫觴,當數賴恩慈2010年的《1+1》(獲鮮浪潮大獎及最佳電影)。電影講居於田園的兩爺孫到城市中到處種竹,批評盲目的興建發展,同時緬懷一種不合時宜、老舊、貼近自然的生活方式。電影非但能破格地在鮮浪潮電影節完結後在商業院線持續放映,也引起不少坊間對政府發展政策、保育問題的關注。2014年是另一個鮮浪潮政治電影的重要年份,該年參賽的《飲食法西斯》( 葉文希導演,獲最佳攝影)與《作為雨水:表象及意志》(陳梓桓導演,獲最佳創意)分別以絕望的未來想像與及揉合現實虛構的陰謀論故事,疾呼對政權的不滿與質疑,贏得不少讚譽。其後兩年陸續出現的《自主時代》(姚仲匡導演,獲特別表揚)、《安琪兒》(陳上城導演,獲最佳創意)、《螻蟻》,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受政治氣候刺激而作的短片。與香港政治社會大事的年譜對讀,不難發現在重要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風波之後(如2009反高鐵、2012年反國教、2014年雨傘運動),都有新一波的鮮浪潮作品回應最新的政治變化與氛圍;鮮浪潮作品與香港宏觀上的變化發展,可謂相當同步。去到今屆,繼續不乏有關政治的作品,而箇中值得留意的是創作者對政治議題的取態與著眼點的變化。以往的鮮浪潮政治短片,無論是強硬地擺出反政府立場還是轉折道出政治上的不平憤鬱,基本上都是一面倒的站在反抗者/受壓迫者/弱勢的一邊。權威/保守勢力/父母輩的描寫要不是全然隱去,就是給簡化成一種抽象、片面、且難以克服的巨大阻力(稍為例外的可能是黃進的《三月六日》);要想像並代入意見相左者的角度,一直都不是鮮浪潮創作者的強項。但這個情況來到今年似乎起了一點點變化。幾部有牽涉政治議題的電影,都不約而同呈現了積極參與、支持社會運動的另一面,道出風風火火地投入抗爭以外/之後的其他社會面相。《出口》(莊文迪導演)講因社運入獄的女生獲釋後與父親相依相處的故事,電影無疑是肯定年青人的犧牲付出,但同時對愛女心切、無法掌握複雜的政治環境的父親深懷同情;電影倒沒有用力地為社運女生說項,反而強調保存親情與獻身社會運動之間的兩難。《渡邊人》(賴永昌導演)用楚漢相爭的處境借喻今日尖銳撕裂的政治環境,少年想渡江參戰,中年船夫則勸他不要浪費有用之身作無望反抗;電影如辯證般鋪陳雙方理據,老少各執一詞,難定孰是孰非—再一次,電影並不全面擁抱抗爭的熱血與正當性,卻突出了對同一事情的正反觀點與及難以論斷的矛盾。至如《下雨天》(曾慶宏導演,獲鮮浪潮大獎)和《白沙堆》(楊兩全導演,獲最佳導演),都有部分篇幅提出一種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再評估,嘗試涵蓋更多種對這幾年香港的政治變故的感想與觀點。雨傘運動後至今三年有餘,年青創作者在政治相關題材上也似乎步入了一個反思、沈澱的時期;直接坦白地批評政權或高呼政治理念的已減少了,更多的是帶著一種猶疑躊躇、難言得失的態度,與及對政治抗爭風眼之外的人物世情,有更強的興趣與關注。這一種路向會不會孕育出真正能成熟而有智慧地討論香港政治的作品,尚是未知之數;但願創作者的取態不會走向意志消沉和犬儒。
今屆一眾參賽影片之中,我最偏愛的是獲最佳攝影的《燈火》(林熙駿導演)。電影講兩父女在母親逝世後相依為命,戲中父親是一個街燈維修工,經常需要入夜後值班,因此總是錯過在家看顧女兒的時光。每年講述這種倫理人情的鮮浪潮作品都有一定數目,初看《燈火》時也有點不以為然,但接連看到幾個充滿實感細節的修路燈畫面,與及看見電影巧妙地建立起燈光/燈火的視覺主題,就開始感受到它的出眾。戲中女孩床頭的燈泡壞了,多番叮囑父親給她買個新的,但父親忙於埋頭苦幹,總是忘了。電影很能寫出父親每晚在外頭為他人燃燈照明,卻無法助女兒於黑暗中的諷刺與淡淡憂愁。電燈的母題之後拓展出女孩為班房中囚於寵物箱的蜥蜴開一盞燈,與及女孩夜遊舞火龍盛會的場面(該段點化相米慎二作品《搬家》結局,略得原作神采,而且整段的拍攝甚有難度,很是令人佩服),箇中的豐富變奏,扣連得緊密精彩。《燈火》還有一個成熟的地方,就是它沒有過份渲染喪親的傷痛,或空泛地聚焦這種悲傷;電影非常踏實地描寫父女倆在變故之後如何應對日常生活,對逝者的感懷反而是低調沉著。
另一部同樣教我擊節嘆賞的作品,是楊兩全的《白沙堆》。故事發生於海南,講一家四口與小叔聚首祖家,準備替過身的嫲嫲立碑。電影的五個角色全都個性刻劃鮮明,各佔若干篇幅,中間還有一場五人聚首晚飯的重要場面。這樣的格局在劇本編寫、演出處理與場面調度上都不輕易。《白沙堆》選角非常準確(這是很多新導演都會忽略的環節),全部演員都有高水準演出;我很喜歡編導將寡言但每開口則多中要害、對妻子稍不耐煩的父親,配搭上一個日夜嘮叨、諸多挑剔的母親,很有火花。演父親的李英濤外型英偉穩重,走出來自有一種家族長者的風範;他重感情、守信諾,行事恪守原則,有些事情他不掛在口邊但心中有數,這些特質由李英濤演出來很是可信,會讓人暗暗敬重這位老者。父親在立碑後下跪,暗自神傷淚垂,讓觀眾看到這硬漢內心柔軟、激動的一面,也很是有感染力。《白沙堆》表面節制、含蓄(我特別喜歡電影寫女兒其美是同性戀的一筆;電影暗示她的同居伴侶是女性,但始終沒有說破,這樣就令其美受母親催婚的部分更加有力,也突顯了她的難言委曲),但內裏卻包含了每個人物經年累積的前事感懷,與及暗湧波濤處處的人情交匯。
對於奪得大獎的《下雨天》,我倒是有一點意見。電影用一個二十分鐘的靜止長鏡頭,同時拍攝三個比鄰的空間:大學宿舍的地下大堂,兩個位於一樓的房間。創作者把宿舍地下與一樓變作猶如舞台的空間,輪流上演學生情侶吵架、大陸生父母前往宿舍探望、一群從旺角佔領現場撤退的學生休息療傷。三間空間的動態此起彼落,人物來往穿梭,實時鋪展多個從個人牽涉到社會的小處境。從場面調度、演出、內容題旨來說,《下雨天》都是乏善足陳。它唯一值得注目的地方就是它的拍攝形式。然而,如果《下雨天》的形式有任何新意或刺激的地方的話,那麼去到電影的第五六分鐘,這種形式的價值已消磨殆盡,不再有重要意義。電影裏每一部分的故事都薄弱,寫不出什麼深刻或有見地的東西;把這些故事組合起來,用一個靜止長鏡頭包裝,也是無補於事,根本就沒有把影片的任何主題推得更深入。況且,這種全片一鏡直落的做法(不論鏡頭有沒有移動)是否這麼創新,這麼值得褒獎,我也很有疑問。
篇幅所限,其他今屆的好作品如《艷陽天》(葉嘉麟導演,獲最佳編劇)、《火》(何頌勤導演,獲特別表揚)、《離境》(羅昊培導演)都未能一一詳述。獎項是一時,電影是一輩子。不論有獎沒獎,我都相信這些鮮浪潮新導演會繼續朝自己心中的方向走下去。沒多久前,聽到一位前輩在看完《三月的獅子》後這麼說:「以往的電影人有的是傲氣,現在的電影人有的是傲慢。」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說法。兩者的分別嘛,我想,就是傲慢者只看到自己,會覺得只有自己的東西才是最重要;至於有傲氣的人,他會看到比自己更大、更好、更高的目標,那是一種對自身嚴格的要求與期許。說到底,有傲氣的人都是不甘心,都想「爭番啖氣」。最好的已經沒我們的份兒,壞的似乎陸續有來,在這麼一個時候,我的同代人們,我們不如就一起盡力的保有最多的不甘心,做一個最有尊嚴和驕傲的我們,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