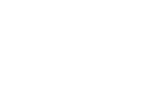如果全都是勝利者,誰會失敗?(文/吳昊)
《摩登牛郎》(Junior Bonner,1972)的優點是沒有半分懷舊的色彩,這使得它和佐治史提芬(George STEVENS)的《原野奇俠》(Shane,1953)或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的《俠膽香盟》(The Lusty Men,1952)截然不同。依然有着畢京柏的世界觀:歷史(時間)把人壓得殘廢。請留意一個場面:Junior駕車到山上找父親,木屋裡有一張模糊的相;牆的一旁是跛子用的拐杖,桌上的破相架有一張騎牛的殘照。Junior這次負了傷回家,不但是形體上的受創(在牛背上翻下),也是心靈的負傷——不如意的過去(在事業的高峰摔交)所留下的苦痛。這一次是歷史造成天地不仁,儘管拼命在牛背上掙扎了8秒鐘,仍然無法超越時間整體。西部是沒落了,畢京柏沒有攻擊機械主義(一向都沒有),只嘲弄了週遭的人;儀仗隊經過,小丑伴着軍人,錦衣牛郎隨着熱狗車,汽車隊中閃出一匹馬來,這個尷尬的時刻響起美國國歌,不知是丑化了西部還是丑化了美國?
畢京柏的人物永遠都是默默的承受着痛苦,有人問到牛郎生涯怎樣,Junior只能答道:「寂寞!」人和動物差不多,受傷的時候要躲回自己的舊地靜養,不同之處在於人這時會感到孤獨。Junior也想起了家。畢京柏懂得以一個破碎的家庭反映社會解體,媽媽不能像舊歲月那樣在吸着煙的時候餵孩子吃飯,舊的文化嬗遞方式在新的社會裡失去作用,沒有人理會懷舊的老父做着淘金夢或者老媽躲在古董店把玩舊西部文物,大家想着的是賣掉了屋子,住流動房屋,不再在泥土上過活。這個打擊實在等如一再的從牛背上摔下。屋子難道是這樣重要?對於森畢京柏來說,屋子是人的外延,早在《午後槍聲》(Ride the High Country,1962)已經告訴大家,人要「名正言順的進入自己的屋子」。這是一種基本的、也可說是自我中心的男性尊嚴;更重要者,這是美國歷史在紅印第安人身上所造成的心理纏擾(歷次的迫害和遷徙使得他們失去本來的土地——和依附於土地上的文化,正如阿瑟潘(Arthur PENN)所說:「現在他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身份,這促成自殺率的增加,和引起近乎自殺——就是酗酒,甚至酗酒駕車。」),有祖父的名字刻於山嶺上的畢京柏自然清楚瞭解自己民族的發展。老父給兒子騙取了土地,自己酗酒撞車,畢京柏顯然是影射美國歷史和被逼害的民族。《大丈夫》(Straw Dogs,1971),堅守自己的屋子,就是要維護自己的尊嚴,激發起一種原始的保衛土地的本能:甚麼都可以讓步,但「這是我的屋子」,一定要寸土必爭。談到了尊嚴,牛主Buck認為他和他的牛都不需要這東西,但Junior堅定的告訴他:「回到家鄉,我是需要這份尊嚴的。」(否則怎可以堂堂正正的進入自己的屋子?)當剷泥車一抓抓碎了木屋(刻着Junior父親名字的郵箱跟着滾翻),就像撕毀了一個人的面孔,第二個鏡頭是剷泥車衝向Junior,再閃接回屋崩瓦潰的情景,Junior逼得把車後駛,是為畢京柏作品中最暴力但最絕望的一刻。
表面看來,《大丈夫》和《摩登牛郎》似乎沒有甚麼相同。一部是狂暴而非人的,一部是溫婉而人性的。人物方面,David(《大丈夫》)是離鄉逃避現實,Junior(《摩登牛郎》)卻是回歸重到人間。雖則如此,細察之下,兩部片相承多於相反,在結構的裡層竟是一次回應。David滿心以為能夠脫離狂暴的美國社會,卻無法擺脫過去的陰影,終於要在異鄉裡以暴力維護自己的尊嚴;Junior帶着過去的瘡疤孤獨地流浪歸家,卻在熟悉的社群裡感到難言的寂寞,要維護曾經是絢爛的過去的一刻(騎士冠軍)就得肯定現在的尊嚴(在牛背上掙扎的8秒鐘);兩個人都沒有選擇的餘地。還有,整部電影的核心是維繫於人類的一個祭禮過程。《大丈夫》,教堂之內進行着宗教儀式,教堂之外狂徒開始祭祀芻狗——人怎樣把自己獻給暴力,電影到了這裡發展成一個恐怖劇。《摩登牛郎》,邊疆日適逢國慶,從華而不實的儀仗隊中你可以看到西部已為文明接收,而在謀利的商業賽會中還有人奉獻西部的傳統精神與德操,電影到了這裡發展成唐吉珂德式的鬧劇。這都是一個很傳統的西部片的兩面性處境:槍手流落異鄉,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逼得大開殺戒(《大丈夫》);回家鄉又發現與一切脫節。要在人們心中重建自己過去的地位,顯然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摩登牛郎》)。只是《摩登牛郎》在題材上不及畢京柏前作[《流寇誌》(The Wild Bunch,1969)和《大丈夫》]的驚世,但既然《荒漠怪俠赤手闖天涯》(The Ballad of Cable Hogue,1970)能夠說清教徒給西部帶來資本主義精神,而現在要說西部的沒落,則又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只有當西部向文明讓步,牛馬競賽會才變成最後一個考驗騎士勇武的地方,你能夠馴服野馬狂牛,一如可以征服往昔的西部。說實在點,西部的沒落是出於自然辯證的毀滅:人類雖則征服自然,而其損毀的程度足可影響將來人類社會的發展。Junior和兇牛「陽光」(Sunshine)的恩怨只是辯證(自毀)模式的個別的例:「沒有馬是騎士所不能騎的,也沒有騎士不被摔下馬來。」所以,畢京柏的人物始終是在直接或間接的自毀死胡同打轉,雖然生命會有間歇的絢燦的時光,就正如《大丈夫》的David在暴力的過程中觸及人性,又或者Junior在孤獨的受創之餘重到世間,也都只是瞬息的生機。《摩登牛郎》的Junior和《義氣雄風》(Wild Rovers,1971,布力愛華士 Blake EDWARDS的傑作)的Frank(賴恩奧尼路 Ryan O'NEAL)是相反的人物,負傷使前者觸及人性,使後者丟掉性命。Frank還沒有給財迷了心時,永遠懷着一個生命(懷中藏着一頭小狗),到後來身上埋着一顆子彈。這兩部電影依然是今年最優秀的西部片,除了都以美國社會解體為對象之外,也都罕有地描寫了近乎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筆下那種破碎的美國家庭,而且兩者皆能刻劃一老一少的傳統西部人物的情誼(《義氣雄風》的Ross和Frank,《摩登牛郎》的兩父子),他們結集了師徒和父子的關係,遵守舊一套的法則,在一個無以容身的天地裡自創生存方式。一個動人的場面:Junior父子闖出了儀仗行列,驅馬越過人家庭院,給曬衫的鐵線絆得栽觔斗。同樣動人的回憶場面:生前的Ross和Frank一起捉馬,慢鏡頭帶出芭蕾舞的美態。可惜的是,他們再沒有機會創造自己的空間。
火車站一個人都沒有,這條鐵路曾一度是個荒原,看它伸向不知名的地方,你站在這端說要遠征澳洲,他站在那邊痛苦於自己破產得不名一文,一架馳來的火車暫時堵塞了兩個人距離之間的空隙。走吧,如果要創造自己,終結是疲於奔命:「這世界如果全都是勝利者,又有誰會失敗?」
(原載於《中國學生周報》第1056期,1972年10月13日,頁10。文章經統校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