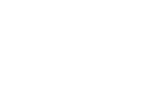文明的祭品——試看森畢京柏《大丈夫》(文/梁濃剛)
到目前止,森畢京柏共拍了六部電影。我個人較有印象的,是從《流寇誌》(The Wild Bunch,1969)開始的三部。《流寇誌》之前的三部,兩部沒有看過,看過的一部[《精忠英烈傳》(Major Dundee,1965)]也印象模糊,記憶不清了。
以此而言,我覺得《大丈夫》(Straw Dogs,1971)是森畢京柏的作品中震撼力最強的一部。由中段的輪姦開始,影片劇力漸次收緊,力迫觀眾的情緒,最後一氣而下,令人絕無喘息的餘地。尤其最後一場,觀眾與困在石屋中的荷夫曼(Dustin HOFFMAN)同舟共濟,大家都是怒海中的一葉輕舟,生死存亡,已不容我們多所選擇。直到最後,主角雖然化險為夷,但是我們離開影院時,感覺中這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表面看來,《大丈夫》不過是繼承《流寇誌》所說的:「這是一個狂暴的時代,我們必須表現它狂暴的一面」這個主題,作更進一步和更徹底的發揮。但是,《大丈夫》所展現的世界觀,比之森畢京柏其他任何一部作品都完整。不錯,它依舊貫穿着森畢京柏舊有的多個主題,例如他對文明的厭惡和對宗教的輕視等,但是這些主題在《大丈夫》中卻獲得更完整和更緊密的結合,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森畢京柏的世界觀。從這個意義說來,《大丈夫》的暴力表現,和《流寇誌》的暴力表現,意義便不相同了。
森畢京柏把我們帶入一個原始的和赤裸裸的暴力世界中。在狂潮迸發的一刻,我們幾已接近暴力的本質。但是,森畢京柏的暴力觀,是建基於他的整個世界觀之上的。影片結束時,荷夫曼扶着白痴的大衛華納(David WARNER)上車,汽車駛入和消失在黑暗之中。這黑暗好像是永恆的黑暗,也像是人類命運的最終歸向,任何形式的救贖都是不存在的。森畢京柏這種悲觀的論調,在以往的作品中並沒有這樣強烈的表現,但在本片卻是表露無遺。森畢京柏既對人類社會失去信心,我們自不能期望他會提出任何改革的方法。這和他的悲觀,又可說互為因果。另一方面,森畢京柏也在他的作品中三番四次地嘲弄宗教信仰。對人對神,他都是同樣的不信任。而看深一層,我們似乎可以說:森畢京柏的作品有着濃烈的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學說的意味,而單就對人類進展的悲觀看法程度來說,森畢京柏比佛洛依德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丈夫》開場的幾個鏡頭,有這樣的情況:一群小孩子手牽手圍着一塊墓碑團團轉,另有一個則坐在另一塊墓碑之上,彷彿跌入沉思的深淵中,森畢京柏的視覺處理總是有着它的二重矛盾性,這一點在他以往的作品中已經是這樣。但是這次,我們卻可以為這種二重矛盾性找到圓滿的解釋。小孩子是生氣勃勃的,把他們放在墓碑的旁邊,這是極其不自然的對比。然而,孩子們圍成一個圓圈,繞着墓碑而走,便有了這個意思:生和死是一個緊緊連扣着的環子,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自然也更加沒有進展可言。坐在墓碑上的那個孩子,神情肅穆,好像他已在推敲死亡的意義。孩童這段時期,在佛洛依德學說中,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簡單說來,孩童是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間,在成人照顧之下,他們毋須接觸殘酷的現實世界,而可以充分沐浴在他們無憂無慮的天地中。然而,人是永遠受着生和死這兩種本能的衝突所糾纏的。年紀愈大,感覺便愈強烈。再照佛洛依德的解釋,成人的行動不過是重複兒童時期的形態,而回復童年這個慾望,在成人潛意識裡尤其強烈。當然,佛洛依德對童年還有一個重要的看法。那就是:人的性本能在童年會得到更充分的發展,成年後,性本能反而受到抑壓。而人類文明進展的原動力,也就是基於人類的性本能永遠的受到抑壓。
嘗試以佛洛依德的學說來解釋森畢京柏的作品,並不是因為他的電影中經常出現很多的兒童,而是這個角度,可以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解釋。《流寇誌》開場是一連串平行的剪接,一方面是一群以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為首的流寇策馬入城,另一方面則是一群兒童,他們流露出天真的眼神,但在腳下他們正在圍觀蟻群侵蝕毒蠍。這幾組兒童和成人對比的鏡頭,現在看來,含義便更清楚了。《大丈夫》開場的兒童遊戲情況,對解釋整部電影有着重大關係。森畢京柏雖然並沒有像佛洛依德那樣來解釋兒童的複雜心理,但他似乎是說:從兒童到老死這個過程中,人類的命運是有着其必然性的。正如兒童手拉手圍繞着墓碑奔走所暗示,死亡的力量潛伏在生命的裡頭,而在生和死的衝突中,暴力的滋生便成為必然和無可救藥的發展。
從這個起點,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看看森畢京柏的整個世界觀。他的人物總是落在時代之後的,換言之,他們拒絕與文明並進。例如《流寇誌》的一群流寇,隨着西部的逐漸結束,他們開始失業,舊有的價值觀念已不適應新的時代。最後,他們為了堅持自己一套似是而非的觀念,竟以一場大屠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荒漠怪俠赤手闖天涯》(The Ballad of Cable Hogue,1970)的主角(謝遜羅伯斯 Jason ROBARDS)最後疑真疑幻地死在一輛汽車輪下,讓文明對他的生命作出了斷。但是,這個主題雖然在森畢京柏的作品中一再表露,它似乎未真正與影片結合為一個整體。所以,有人解釋《流寇誌》的道德價值是矛盾的道德價值。但在《大丈夫》中,森畢京柏的各個主題終於開始互相連扣在一起了。如果,文明的進展果如佛洛依德所說,是基於對人類性本能的抑壓,那麼文明本身固然有其可厭惡的地方,而抑壓人類性本能尤會造成暴力的發洩,而這股力量最後終會摧毀文明。在另一方面人類靈魂的救贖則無從說起,因為宗教信仰拆穿了不外是騙人伎倆,對於消解人性潛伏的暴力,宗教是無能為力的。
德斯汀荷夫曼演的數學家,為了逃避美國的暴力社會,利用他放長假的機會,攜妻遷往英國一個郊區小村落。森畢京柏相當悲觀,個人在偌大的社會中竟無容身之地。但正如影片的發展所證明,暴力是人類社會潛在的特性,避是避不開的。在這裡,厭棄文明的主題又再度出現。首先,是荷夫曼的車房需要蓋頂,種下後患。他的烤麵包機壞了,又無法修理。這個代表文明一分子的荷夫曼,事實上他連生活的基本問題都不懂得對付。他開車時欲速不達、手足無措的情況,看來不是十分尷尬嗎?而在一個比較原始的社會中,他既有的文明反而變成一種軟弱。別人從車房屋頂跳下地,他卻要沿梯而下,文明進步,人的軀體本能卻退步。最後一場戲可說是全片劇力積聚的頂點。荷夫曼夫婦兩人被困屋內,屋外是一個濃霧瀰漫的黑漆世界,五個完全喪失理性的人,擲石毀窗、縱火燒屋,接二連三地以一連串原始的狂暴行動宣洩他們潛伏的暴力。有一個屋外的鏡頭,兩人爭奪一輛自行車(和汽車比較,這是落後的文明象徵),然後兩人轉身入車房再取一輛,雙雙踏着自行車而出,並且尖聲怪叫。屋內的光線映起層層大霧,好一幅人間地獄的寫照!這個鏡頭如鬼魅之突然出現,令人不寒而慄。這是森畢京柏以往作品中所絕無僅有的。
再分析這個小村落的人。每個人都有着某種不正常的抑壓。在《荒漢怪俠赤手闖天涯》中演牧師的大衛華納,森畢京柏讓他在片中演一個白痴。在某一程度上說來,白痴可以解釋為延長童年時期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構成對他們脫離成人社會的一種保障。所以到最後,影片死了七個人,他卻安然無恙。被他失手勒斃的少女;本身和她的弟弟有着某種不正常的「姊弟」關係,根據佛洛依德的解釋,這無疑是抑壓性本能的現象之一。此外,修理車房的四個男人和女主角蘇珊翠芝(Susan GEORGE)本身,他們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受着性慾的支配,並且直接促成他們行動的本身。蘇珊翠芝被輪姦的一場,表情混合着痛苦和快樂。在這一刻中,森畢京柏使我們面對面,避無可避地接觸了人類宣洩抑壓的性慾的情況。
威廉荷頓的一群流寇明知必死而赴難,他們的道德抉擇是相當令人懷疑的。謝遜羅伯斯莫明其妙地死在車輪下,這樣對文明的厭棄,也似乎大可不必。同樣,德斯汀荷夫曼死守石屋的原則,也會令人懷疑。何況,我們知道森畢京柏佈置這個處境,不外是引伸人類學家羅拔阿德里(Robert ARDREY)的一個論點,就是說:人類自古以來,即有着搶奪和霸佔土地的本能,這種本能和人類的性本能大概有着同樣久遠的歷史。所以,可能有人認為森畢京柏仍未為他的暴力表現找到真正的藉口。但是我認為,森畢京柏的幾個主題在本片已相當完整而吻合地構成一個統一的世界觀。本片的暴力手段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竟有這樣瘋狂和殘暴的獸性一面。人類固然難望救贖,潛在的暴力也無從消解。正如片中的胖老頭對獨臂法官(形同虛設的法律)說:「我就是我。」人性是無可改變的。而在所謂的文明的進展過程中,人反而變成了祭祀品。森畢京柏悲觀的世界觀相信很難令人接受,但縱然這樣,本片的震撼力仍足以令你離開影院時四肢無力。
(原載於《中國學生周報》第1029期,1972年4月7日,頁10。文章經統校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