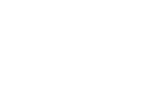稻草狗──不談暴力,還能說些甚麼?(文/吳昊)
「芻狗者,祭神之物……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魏書‧周宣傳》)
《大丈夫》(Straw Dogs,1971),不談森畢京柏的暴力,還能說些甚麼?
三十五分鐘無政府主義的毀滅和人類的暴虐相殘,你只能癱瘓的頹倒於椅上,給眼前的影像驚得手足無措。這一個狂暴的場面是極度壓迫性,(自然得助於出色的割接技法),再不容許你有思想的餘地,只是被動的牽着走(也不會懷疑一個人能否有足夠的力量殺死五個狂徒),怎樣也無法跳出來剖析事態的解決應否訴諸暴力(作出道德上的批判)。換言之,在你易地而處的時候(妻子被污,執法者遇害,外面人要殺進來,內面卻又發生兩性爭雄),亦同樣激引起自己獸性的保衛機能的條件反應:殺(否則便要被殺),再沒有任何選擇的機會。如果別些片子沒有做到的話,那麼畢京柏便給你見識他的手段:暴力的價值觀念是可以中性化。
稻草狗是有兩個意義,一指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畢京柏的暴力的宇宙觀,一指犧牲儀式(古中國社會有結草為狗作祭祀之用,正如成玄英疏《莊子‧天運》:「結草為狗以解除也。」)——畢京柏的暴力的社會觀。《大丈夫》那一片荒原野地滿目是自然的蕭殺(氣氛陰鬱,鴉雀無聲,生物不留——偶有亡命飛逃的驚鳥和土鼠),人為的物質世界又是同樣殘缺不全(夫婦的住所的車房未曾搭好,汽車吵得半天才能走動,多士爐拿去修理,鬧鐘斷鏈,槍和獵獸器只掛作牆飾,火爐又從未生起過火),而一個人際的社會又不見得正常(父親粗暴得失去理性,戀弟的花痴女兒,心智殘缺的跛子,幾個色情狂,還有一段行將破碎的婚姻)。《流寇誌》(The Wild Bunch,1969)有着一股愁情,是因為民謠加上宿命,《大丈夫》是滾石一球,機械的運行壓碎你的感官。森畢京柏突然把暴力看成天道(多於宿命),故此片中事件的因果問題並不重要(事情總得要發生),他的仰鏡頭也就比俯鏡倍加有力:幾次以俯鏡網羅地上的人物亦失去定命的感覺,一組仰鏡拍攝天帝(牧師)和誦詩的儀式,你便知道一件例行的「神聖」的事就要施行。David初嘗毀滅的滋味(持槍狩獵),家內的妻子卻受人摧殘,這是他要對暴力所付出的代價,天地不仁之處在此,畢京柏把兩件事情以Cross-Cutting連在一起,彷彿是要說:你在這裡向生命施暴,別一個角落又有人幹着性質相同的事情(很平常吧)。
片子開始的時候,孩子們手拉手繞着墓碑跑,看來就像一個原始民族的祭儀(起先影像是糢糊的神秘),向死亡和毀滅膜拜,森畢京柏總要這下一代的人物見證生命的戰場(《流寇誌》如此),應天之道(可能是和紅印第安人的民族信念有關),從而成長。只有人類才把暴力看成一種祭典,自圖騰主義開始,犧牲和征服變成宗教理想,穿黑衣服持著蠟燭的教士(David引用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話:「流血最多的王國就是基督教。」)向黑暗中談煉獄,教堂以外的狂徒開始進行芻狗的祭儀。大家都陷於歇斯底里的狀況,狂性漸漸萌生,自教堂派對的場面而下,人物的面孔(尤其David)全都變得灰白可怕,事實上下半場戲簡直發展成近乎原始宗教的犧牲儀式,就和恐怖片配上同一張面譜。
這實在是一個很典型的西部片處境:一個人(隱姓埋名的槍手或弱者)多次不願出手,但受到三番四次的折磨,為了維護自身最基本的尊嚴,憤然堅守壁壘拚力而戰。畢京柏在西部以外發展個人對決狂暴的西部處境,無非是要印證自己的世界觀是有其普遍及永恆之處。David退居一隅永遠隔着窗看人,就正如他只從電視機上看動亂的美國,總認為可以躲着過寧靜生活,但世界是隨着一個模式推展:這一面暴力爆發,難免那一方不是如此。這是一個可悲的處境,從David面上的愁容看出他對人間的憂鬱,不時把眼鏡除下來,只希望對週遭保持一個模糊印象。屋子是他的蝸牛殼(他說:「這間屋就是我自己」),屋子和他共有一個生命,同樣的孤獨地守着荒原,外界的暴力慢慢滲入來(先是貓兒被殺,妻子被姦,然後……),漸漸的向屋子瘋狂進擊,屋子默默的乘負着痛苦就彷彿一個生命遇襲受傷,畢京柏把屋子賦予感覺,也就加深了我們的心理負擔(我們躲在戲院的暗角裡失去安全,因為街上的人好像要殺將進來——很不好受)。為屋子而奮起還擊是唯一向自己交代的途徑。在《流寇誌》中我們已經看到對自我塑造和毀滅是分不開。
畢京柏對Humanity有惡的一面看法。David從不願接觸人的問題,才會着迷於天體的互動關係(天文數學),那次和牧師交談是帶着自辯的態度回到社會互動的層面上來(戰爭和基督教的辯論)。把視點從宇宙轉到了人間,本就是可喜的事情,可是一旦如此又便捲進了暴力的漩渦,《大丈夫》給人的詭辯:要接觸人性便得參與暴力,未免過於灰色。你明白了遊戲的規則?要解除心理的魔障,需得找尋代罪羔羊——那就「結草為狗,以解除也」。
《大丈夫》在技巧上得手,未必等如在藝術上有成就。畢京柏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給你支持批判的立場,他抹去故事應有的社會背景和心理背景,也殺害人物之間的關係,顯然是過於自覺的要將暴力這個原始現象重行一次的從Microcosm推展為Macrocosm。畢京柏實在也太極權,以暴烈的影像硬逼着人,那股專橫的氣勢已經淘去了藝術家的情懷。《大丈夫》及不上《流寇誌》就因為少了一分人的感情。由此亦可看出片子頗為弱於境界。畢京柏過於利用《大丈夫》顯露他的暴力手段,那麼就應該緊記芻狗的寓言(目標達成手段即無價值):芻狗一經祭神之後,便棄之為廢物,給車載去作柴燒掉。
(原載於《中國學生周報》第1029期,1972年4月7日,頁10。文章經統校和修正。)